《艾约堡秘史》:正在被揭示的神秘世界
来源:文艺报 | 李亦 2018年06月27日08: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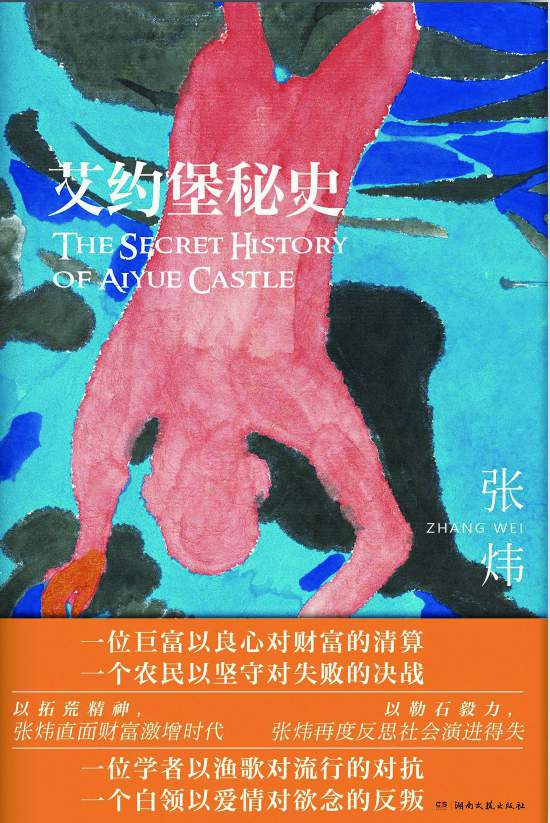
叙事性文学,尤其是小说,必有不同情形的神秘性杂糅其中,这是潜在的阅读需求。许多创作实践证明,神秘性是创作一部作品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张炜的《艾约堡秘史》有足够的神秘性,它的神秘性不在于题材,也不在于故事,而在于作者创造的常人难以探察和深入的精神城堡。它折射出我们这个时代一些不为人知的神秘角落,由此也让人看到作者内敛到禅宗般的安静和非凡的创造力。
从头看来,这部小说以“艾约堡”这样一个极具神秘性和象征意义的地点展开故事,这很容易将读者带入浓郁的“城堡”小说氛围中,但“艾约堡”不是城堡,“艾约堡”里住着的人也不是19世纪甚至更早的洋毛儿,“艾约堡”住着一个叫淳于宝册的60岁老人以及他创建的“庞大帝国”——狸金集团。小说一开始就把“古堡”和“集团”的意象呈现出来,引人深思。很显然,“城堡”和“集团”都是极具实力的社会组成部分,两者有着极其相似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众所周知,西方贵族催生了城堡生活样式,近现代中国没有贵族,也无城堡,但近30年来的社会发展,让产自西域的城堡在中国沿海某个风光秀美的峡角或大山谷地落地生根了。文化浸染和经济渗透席卷全球,保持文化和经济的独立性已非易事,煎饼大葱和牛排咖啡的相互补充,布鞋和西装的自由搭配已习以为常,基于这样的社会现实,“艾约堡”的出现也就不是杜撰了。
纵观张炜以往的小说,对土地的眷恋和热爱,对弱者的同情和悲悯,对善良的褒扬和盛赞,对邪恶的愤怒和鞭挞,对真理和理想的锲而不舍等意旨都是溢于言表痛快淋漓的,新作《艾约堡秘史》对这一切的判断就没那么简单了。时间和阅历让张炜藏起了锋芒,收回了犀利,斩乱麻的快刀暂且入鞘,他要用手解一解集结错愕的乱麻了。
这团乱麻有一个来自学府的名字:资本。资本有个乳名叫钱,这是所有人都离不开的生活必需,它是人类生存的潜在指挥棒,不仅如此,它还能简单而粗暴地界定一个人的尊卑贵贱。在淳于宝册创建“集团”前很长的时间里,钱并不是他关注的第一要素。没有自尊没有希望的漫漫长路,要不停地“递了哎哟”才能勉强度日,青岛的校长老师李易几乎是他的全部精神支撑,他要上学读书,他要参加学校的诗社,即使在逃亡的路上,他仍有写点什么的冲动和欲望。从起点上看淳于宝册的精神格调值得称道,如果一直葆有这样的格调,也许他真能成为一个不错的“著作家”,但对他来说,能坚持多久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残酷的现实里,岁月能允许他在多大程度上还葆有这样的格调和品质呢?艰难困苦最易产生“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扛起高格调的红旗自然需要某种坚硬的品质,这在作品里都有透露。但他慢慢靠近了资本,并建立了一个“伟大的集团”。表面上看,建立一个“伟大集团”与成为一个“著作家”并不矛盾,他甚至把集团的事务交给别人打理,而自己则安心学术。一个时期里,他还真的有了数量可观的“著作”,并引以为荣。但事实是他离一个真正的著作家越来越远,甚至已经与“著作”无关了。他在朝着自己想不到的方向滑落。他内心的孤独和清苦难以预料,面对资本的惯性和扭力他几乎无能为力了。
或许淳于宝册进入资本生活的道路很不堪,或许这个过程没必要纠结,马克思关于原始资本的论述尽人皆知:每一个铜板上都滴着工人的血。对于淳于宝册来说,无论以怎样的方式聚集的原始资本,那都是过去时了,作者强调的是他的现在,他现在是一个“伟大帝国”的皇帝——狸金集团董事长,他现在的生活才是揭开这个秘密世界的钥匙。
淳于宝册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以他个人对自己的评价,他是一个“歪打正着的人”,他从心里不想做一个企业家,他的灵魂深处埋了另一种志向,“那就是创造出一片心灵的大天地……要用笔记下心里的一切,对这个狗日的世界记下所有的喜欢和厌恶、所有的爱和恨,还有我希望他变成的样子!”但随即他又觉得那是一个狂妄的目标。他憎恶自己以前的角色,这个“以前”很可能就是他创业的过程,“现在想,我可能把心底的力气投错了,所以就有了现在的狸金。它是个歪打正着的产物,一个长大不由爷的孩子,我看都不想多看一眼的孩子。”他创造了狸金,他曾经最爱狸金,最终他却无法与之相处了。他要开始过自己的生活了。他一直想做一个著作家,还想做一个情种。可惜狸金的事务过于忙碌了,最后只落得个业余的“情种研究者”。经历过60多年的风雨,他对集团、对集团之外的许多事物已经慢慢失去了兴趣,“唯有两性间的相吸相斥仍旧让他感到费解与好奇。他甚至认为人世间的一切奇迹,说到底都由男女间这一对不测的关系转化而来,也因此而显得深奥无比。有些家事国事乍一看远离了儿女情愫,实则内部还是曲折地联系在一起。”“天地间有一种阴阳转换的伟大定力,它首先是从男女情事上体现出来的。”
在我看来,在内部与淳于宝册“曲折地联系在一起”的女人不算少,但真正对他产生不可逆转力的却不多。小狗丽闪电般出现在他的生活里,并刻下深深的烙印。蛹儿是个知性女青年,她爱书、读书,这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淳于宝册的精神需求,他有些霸气地将这个像火狐般的女人“招安”了。在她的眼里,淳于宝册不仅是个企业家,还是个学府人物或将军,有了这样的双重评价,蛹儿对他除了拿出应有的尊敬和服从也就没有更多的感召力了。“老政委”杏梅是个具有双性特征的传奇,这个自称“战争年代过来的人”,豪气多于温柔,她抽烟喝酒,吃饭很快,她要把淳于宝册炼成一块好钢。杏梅虽不是宝册最中意的女性,但在精神深处对他的影响却是不可磨灭的。20年前宝册曾认识“一个单薄的女孩,就是因为能够频繁地接触高层男子,竟然在几年的时间里变得成熟,身材也惊人地丰腴,神色含蓄了许多,只是开怀大笑时才显得浅薄依旧。以宝册的经验,他曾训诫自己的孙子:‘那些无耻而颇具姿色的女人毒性最大。’”
欧驼兰吸引淳于宝册的,不是绝艳的姿色,不是五车难载的学识,也不是吸引彼此的拉网号子,更不是她来自省城有着与自己悬殊的文化和社会背景,而是一个眼神。这是来自彼岸的指路明灯,是升华了全部人性欲望之后的纯粹至极的原初本能。至此,这场轰轰烈烈的恋爱已非恋爱,而是人性的回归和朝圣,他的帝国狸金集团和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不能带他回归,他的著作和财富不能带他朝圣,他在这个世界上拥有的一切都显得有些多余,只有那个看上去不像这个世界的人欧驼兰的眼神让他重振已经颓唐的意志,并引他上路了。
《艾约堡秘史》与张炜其他小说一样都是一定意义上的“史”,但《艾约堡秘史》的“史”有一种潜在的特性,没有外形、没有核心;来来去去的人物,你方唱罢我登场,却落得个终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史”是一种无形的力量——资本的力量,一种皈依——精神的家园。
资本有一双神秘之手,它可以改变世界也可以描摹人生。越来越多的人被它的真实性打动并趋之若鹜;资本让越来越多的人从精神家园出走并回头留下最后的轻蔑和鄙视,资本让越来越多的人离开“无用”而投身到极端近视的“有用”中。令人恐惧的资本的力量已经残酷地折磨过狸金集团的淳于宝册,正在折磨渔村矶滩角的吴沙原、民俗学家欧驼兰。很显然,未来还会有更多的人被这双神秘之手把玩戏弄,而最终结果胜败无异,只有精神家园的守望者才是真正的赢家。那可是凤毛麟角了。
写资本与精神的对垒,张炜不是第一个,但能把两者的关系引导到阴阳相合的自然境界,张炜却是第一个。
这就是那个在一千几百万字作品之后还像西西弗斯推石上山一样的张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