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文学》陈集益:每个真正有理想有追求的写作者,都想成为“硬菜”
来源:《野草》微信公众号 | 2018年06月21日09:40

陈集益,1973年生,浙江金华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于鲁迅文学院高研班学习写作。有小说《城门洞开》《吴村野人》《人皮鼓》《制造好人》《驯牛记》等一百万字,见于《十月》《人民文学》《钟山》《花城》等刊物。出版有小说集多部,《野猪场》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10年卷。现居北京。
朝潮:从同学到朋友,我们相识整二十年了,一直是平平淡淡。跟别人交往中,你最害怕或厌倦什么?
陈集益:是啊,我们是在1998年秋天认识的。那时候我们还是小青年,在杭州西湖边的半山腰参加文学培训,每天晚上要到西湖边转一转,浑身是力气,猴子一样蹿上蹿下,如今突然就老了。那时候我还没有开始写作,只是有这个想法,机缘巧合去了这个班,感谢盛子潮老师、任峻老师,还有你和朱坤宇等等,当初对我的鼓励。我是从杭州回去以后开始看书和练笔的。你后来好像来金华找我和朱坤宇一块聚过。再后来,BB机大家都不用了,就没有联系了。没想到后来我们因为还都在写作,就又联系上了。
你问到与人交往的问题,其实我是个有轻微社交恐惧倾向的人,假如有一天,我有了合适的条件,从人群中消失,十年二十年后再回来,这也是能做到的。因为整体上来说,我是个喜欢独处的人。喜欢安静。最好不与人长时间交谈。一是因为我心里空空荡荡的,好像从来就没有必须跟人要讲的话。二是真要交谈起来,我说的基本上是实话,老说实话的人其实很傻,而后,就会后悔;说假话呢,更后悔。所以跟别人交往中,比较害怕一屋子人都在说套话,待会轮到自己说点什么好呢。
朝潮:很多作者眼里,编辑很少看自然来稿,只发熟人的稿或约稿。你有什么话要说?
陈集益:关于这个问题,每个编辑部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每个编辑的情况也是千差万别。有的拨款多的杂志,编辑一大屋子,劳动力大量剩余,一般而言,像这样的单位自然来稿领导规定是要看的。但是没钱的编辑部就不一样了,只有一两个编辑在做事,忙得像鞭子抽打着陀螺转,自然来稿就很难保证都看。这其实是能理解的。就我本人,就经历过这两种情况。我以前在一个钱多的编辑部,我的任务就是看自然来稿,也就是说,我每稿都看,大多数回复。日积月累的,没想到在自然来稿里发现了很多所谓的新人和好的苗子。不但如此,我还到网上主动地去发现作者。当初这些作者都不太出名,现在有不少已经是优秀的作家,有的还是名家了。
关于一些不得志的作者,容易与编辑产生敌对情绪,站在作者的立场,也能理解。毕竟每写一个稿子要花费太多心血。有写长篇的,可能要花去几年业余时间。但是一个作者来了灵感比如构思了一篇小说在家埋头写作,跟杂志并不构成什么必然联系(除非是特为杂志约稿而写),杂志方面也不存在必须要发表这篇小说的义务。在杂志方面,每个编辑只是按照领导的要求寻找杂志需要的作品,一是文学杂志也是媒体,要完成文艺宣传功能、舆论导向等政治任务,二是让花钱订购杂志的读者能读到更好作品,明年接着订,杂志越办越红火,既完成经济指标,又变成品牌;杂志为了达到这些目的,总是希望拿到符合杂志定位、读者喜闻乐见的作品。与此同时,这个寻找过程中,编辑当然也希望发现新作者,培养自己的作者队伍,其实也不过是为了上述目的,比如在名家出名之前先建立这么个联系。这跟上百年前几个同仁凑一笔钱出一本什么杂志,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假设,有一个作者写得平平庸庸,又让人看不到他将来有什么大发展的可能,自然会被编辑部冷落,因为从属性来说,文学杂志毕竟不是文学培训机构。很多作者希望通过投稿,让编辑来指导他写作,甚至帮他修改作品,除了这个编辑自愿以外,有编辑不愿这么干,也不能说他失职。也有的作者写出了政治敏感、宗教敏感、严重违背道德伦理的作品,因为遭到某编辑拒绝,而对接稿编辑心怀不满,这显然有失公允。编辑没有义务为了这个作品去蹲监狱,除非他愿意为你牺牲自己。
最后说一下关系稿这个话题。这情况有点类似我们去饭店吃饭,一大桌子,荤的,素的,花花绿绿,其中几个硬菜无疑是这顿饭的兴奋点,也是最有营养价值的,然后吃着吃着,服务员突然端来了一碟什么东西,说是今天老板过生日,饭店免费赠送的甜点。这个东西的基本卫生肯定是达标的,吃了一般不会拉肚子,否则谁也不好意思端上来,但是说这东西要比硬菜还要有价值,这个不太可信,否则不会以这种形式出现。具体到编辑工作,底层编辑想发一个关系稿其实挺难的,因为要过好几审,一般过不了关,但是就像吃着饭,突然来了一碟莫名其妙的甜点,这个跟底层编辑没有什么大关系。好在饭店老板过生日这样的事情,不是每天都会遇到,他添的那道点心对一大桌子饭菜也造不成多大影响。所以遇到这种情况,不论编辑还是读者或者其他作者,都相互体谅一下吧。我想一个真正有理想有追求的写作者,不会都想做这样的“点心”的,成为“硬菜”、被食客盼着吃才是硬道理。所以,还是希望那些暂时还没有得到太多认可的作者,写的时候不要老想着杂志发表这回事,等到认真写完了,再考虑合适的杂志投稿,这家不行再换一家,这个不行再换一个。如果你真写得好,只有要耐心、诚意,总能遇到一两个欣赏你的编辑吧。现在文学杂志如此之多,不太可能每家都不看自然来稿。如果实在遇不到,也不屑于再投稿,甚至最后连写都沉不下心来,带着情绪。那么,这就本末倒置、朝着不利于创作的方向发展了。
朝潮:做文学编辑有哪些苦衷?
陈集益:苦衷做任何工作都会有的。我这一生做过不少工作,好像还没有遇到特别舒心的。关于编辑这个职业的苦衷,其实在上面基本说到了。我的想法是,我是到了一大把年纪才决定做这行的,既然进了这行,有苦衷也得自个忍受。再说,从事编辑工作也是有苦也有乐的。
另外,我在这里给你灌一碗心灵鸡汤:我在北京坐公交车很多年,一般情况是,每个售票员都绷着脸,没有好声气,有的蓬头垢面,有的报站含含糊糊的,根本听不清卷舌音后面说的是什么。但是有一天,我带着孩子挤上了一辆特别挤的公交车,售票员一看孩子得抱着,立刻帮我嚷嚷有谁让座,结果那天也是巧,车上大部分是老年人,我不可能让他们让座。售票员灵机一动,就在车前头,下面可能是搁发动机的地方,有一个方形大木箱,她就找来一块纸板,让孩子坐在上面,孩子坐得稳稳当当的,一路很高兴。售票员在工作的间隙,偶尔还逗孩子说话,她的脸上始终洋溢着劳动的快乐、为乘客服务的热忱。我感动了一路,一个看起来挺卑微的职业,在她身上折射出高贵的美,乘客自然也会客客气气的。我想,既然做了这个工作,要么尽心尽力做好,要么就不做。不能因为各种原因,就像前面提到的那些含含糊糊的售票员那样敷衍,偷懒,恶性循环。
朝潮:私人阅读中,哪些作品打动过你?
陈集益:你说的是阅读世界名著之类的吗?我去年读《修道院纪事》,作者写着写着,突然停了下来,捎带着写到有一块石头,是一块路基,应该是早一年铺在那儿的,冒出一句:“经过一个严寒的冬天,阳光第一次照耀到这块石头……”当时眼眶就湿了。还有《日瓦戈医生》,写一队苦刑犯被脚镣拷在一起,他们被卫兵赶着走路,作者突然来了一句:“他们齐步向前走,每一迈步脚镣便一齐哗啦啦响。他们都是亡命的和绝望的人,像天上的闪电一样可怕。”我感觉这闪电的比喻既是源自脚镣发出的刺啦刺啦声,同时源自脚镣被牵动时上面磨得锃亮的地方折射了光,这就是大师手笔。总之因为时间原因,我现在阅读越来越少,有时候读几页,内容全忘了,只记住这样一些打动过我的句子了。
朝潮:一拔拔年轻作者从《青年文学》走向中老年,杂志一直保持“青年”的特性和活力。你觉得,一位写作者应如何保持“青年”状态。
陈集益:《青年文学》现在的作者年龄以40岁以下为主,尤其欢迎80后、90后投稿,所以整个状态看上去确实挺年轻的。这就跟大学校园里,不管多少人毕业了,总是有那么多背着包的年轻人走来走去。
具体到我们自身的“中年写作”,目前好像还真看到了一些变化。一是整个相貌,有点让人伤感,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变成中年人的样子了,只有老兄还是这么年轻,我有时看微信,看见你的照片,几乎没变;另外就是有一部分中年写作者的文字好像也随着年纪大了,开始失去灵性,也就是那种想摁都摁不住的野性没了,刺啦刺啦的跳跃性语感没了,不按常理出牌的结构没了,总之变得结结实实、老成持重起来。每个年龄做各自年龄的事,我倒不觉得一定是坏事。年轻的时候,写小说爱玩点花样,语言火花四溅的样子,当然是好的,然后到了中年,走个过街天桥都喘气了,硬要去学着年轻人跳街舞,会有点吃力。我想保持“青年”状态,唯一能保持下来的是思想上的尖锐吧。这尖锐不一定是王小波那种很炫目的样子。但是我们作为中老年作家,必须要继续保持思想锋芒,要继续保持对社会的责任感,对疾苦人群的悲悯情怀,对现实社会的批判精神,对政治的敏感,对强权的警惕,对人性的拷问,等等。希望我们的思想,比肉身衰老得慢一些。比如高尔泰、杨显惠等等,他们中年后的写作状态,值得我去学习。
朝潮:请你给年轻的写作者提供一些作为文学编辑的建议。
陈集益:如果一定要说,就是写作主要是自己的事情,其实就是自己的事情,不要过于在意编辑怎么看。哪一天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编辑突然从这个星球上消失了,该写作,我们还得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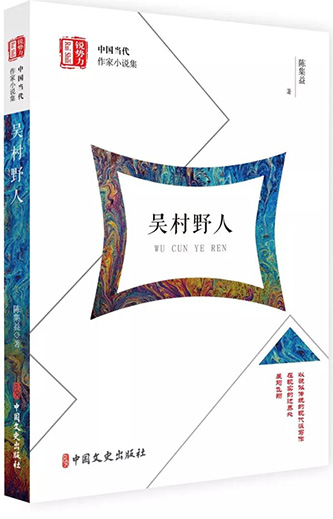
作者:陈集益
出版:中国文史出版社
版次:2018年5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内容简介: 小说集《吴村野人》由六个中篇小说构成。故事题材皆来源于作者的出生地吴村。内容介于现实与幻想之间,构思奇特,想象汪洋恣睢。现代先锋的创作手法结合传统现实主义的叙事语境,故事夸张变形之中不失幽默诙谐,情感冲击酣畅淋漓:野猪、家猪、杂交猪,真人、野人、假野人,文明人、野蛮人、癫狂人,妻子、父母、兄弟,叙事对象由温驯到粗野的裂变,由亲情到冷酷的隔膜,由爱恋到杀戮的疯狂……人性的诡异多变与兽性的肆无忌惮在文字里交相辉映,在杂交猪变为野猪、真人成为野人、父母兄弟反目成仇的故事背后,展示给读者一幅宏大叙事的世俗疯狂图景,读后令人拍案惊奇。


